有这样一个故事:古时候,两个沙漠中的和尚,立誓要永远住在寺院里。虽然他们曾发誓要永远呆在寺院里,但他们也渴望去旅行和探索无法企及的世界。
因此,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。
每隔六个月,他们就会坐下来,精心制定去世界某个地方旅行的细节。每个细节他们都考虑过,计划是完美的。
一旦他们“完成”了自己的计划,他们就会回到自己的岗位上,六个月后,他们会计划下一次旅行。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享受着这种可能性带来的兴奋,而不必将其变为现实。
无处不在的抵抗
你真的想改变吗?
有趣的是,对很多人来说,尤其是那些有新年计划的人来说,我们的行为和沙漠僧侣非常相似。我们非常期待和渴望改变,甚至会迈出第一步,去设想、肯定和定位我们自己的目标。在做出改变这个单一决定的背后,有一种意志力的力量。但是意志力是不够的。
在我们解决其他问题之前,我们必须考虑为什么意志力是不够的。答案是,因为我们非常抗拒改变。在改变的阶段,最大的指导方针之一是了解你的障碍,当我们考虑我们对改变的渴望与我们缺乏实际做出改变的倾向时,我们应该很好地认识到阻碍我们前进的阻力。
当我们考虑改变的障碍,以及为什么意志力、肯定和目的性是不够的,我们必须从承认人类面对改变的普遍困境开始:
我们不喜欢改变。
我们会抵抗新事物,质疑新事物,火车和电视等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东西在最初出现的时候,都曾受到过质疑。我们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抗拒变化的倾向。
改变是自然的,但我们也会自然地抵制它。
为什么?
实际上有三个原因,如果我们要克服改变路上的这些障碍,我们可能需要了解这些原因是什么。
原因1:改变是破坏性的
让我们从社会学开始。决定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力有两种:可预见性和稳定性。人类对自己的行为倾向于天生保守,因为我们追求秩序、一致性和熟悉感。这不是一种批评。人类的目的是生存,如果你想要活下去,维持你的部落,延续你的基因,不确定性和混乱是没有帮助的。我们天生就要寻求安全。
我们害怕未知。
比起未知的领域,我们更喜欢熟悉的领域。
这里也有一个生物学上的例子。我不是认知精神病学家或神经科学家,所以我的描述听起来会很外行。大脑大致由三个同心圆组成,有时也被称为三位一体大脑。每个圈包含了不同的部分,从内到外一层比一层复杂。“三位一体的大脑”(triune brain)假说是Paul MacLean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理论,此理论根据在进化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,将人类大脑分成“爬行动物脑”(Reptilian brain)、“古哺乳动物脑”(paleomammalian brain)和“新哺乳动物脑”(neomammalian brain)三大部分。
大脑的最外层是新哺乳动物脑,提供了理性思考、归类意义和经历复杂决策过程的能力。只有最聪明的生物才有这种能力,当然,人类拥有这种最复杂的能力。
中间部分是古哺乳动物脑,即边缘系统(limbic system)。人体的哺乳脑,和所有哺乳类的大脑,在本质上并无二致,包含感觉和情绪,拥有玩乐的欲望,也是母性的来源。这一层大脑用来生成各种情绪,包括最基本的恐惧、兴奋等等,这样的情绪,实际上是对各种外部刺激的高级综合反应,感受到危险要产生恐惧,以便迅速逃离;见到猎物要足够兴奋,以便身体各个部分协调起来足够有效率。
大脑最里面的部分是爬行动物脑,它能控制生命基本功能,如心跳、呼吸、打架、逃命、喂食和繁殖等功能。这一层大脑,它们没有情绪,没有理智,只有5种应激反应,保障你的生存。即使是蜥蜴也有这个部分。
换句话说,你的大脑中有一部分使你安全的活着,尽可能多的追求可预测性和稳定性。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制度、方法、规范、价值和程序来让生存变得更容易?因为熟悉可以帮助我们减轻不确定性。如果有人开始改变那些既定的剧本,就是在搅乱我们的场子。
马歇尔·斯科特·普尔(Marshall Scott Poole)描述了一种理论,该理论有助于解释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出现的,它被称为“结构适应理论”(Structural Adaptation Theory)。本质上,文化集体寻求可预测性和稳定性,以确保我们的生存。我们创造结构和社会系统,即之前所谓的剧本,让生活更容易。然而,在创造一个结构的行为中,我们改变了现实的面貌,然后,必须创造新的规范、规则、系统和结构来补偿。
以互联网为例。它的创建是为了简化和加快交流。它给出了一个结构。然而,从一开始,它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不确定的世界,导致新的结构的建立。根据普尔的观点,这个循环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。这就是为什么文化总是在变化的。
另一个例子是乌里·布罗芬布伦纳(Urie Brofenbrenner)的生物生态系统理论(Bio-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)。布罗芬布伦纳是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家,他试图解释人类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是如何存在的,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分为不同的层面。
布朗芬布伦纳认为,自然环境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影响源,这一点往往被人为设计的实验室里的研究发展的学者所忽视。他认为,环境是“一组嵌套结构,每一个嵌套在下一个中,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”。换句话说,发展的个体处在从直接环境(像家庭)到间接环境(像宽泛的文化)的几个环境系统的中间或嵌套于其中。每一系统都与其他系统以及个体交互作用,影响着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。
环境层次的最里层是微观系统(microsystem),指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,这个环境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,是环境系统的最里层。这一层级包括与你亲近的人的互动,包括与家人、朋友和你自己的经历。
第二个环境层次是中间系统(mesosystem),中间系统是指各微系统之间的联系或相互关系,如社区、团队、工作或更大的团体。
第三个环境层次是外层系统(exosystem)。是指那些不是我们生活的直接组成部分,但也能影响我们的系统。例如,对儿童来说,父母的工作环境就是外层系统影响因素。
第四个环境系统是宏观系统(macrosystem),也就是一般文化。布罗芬布伦纳说,这是最强大的,因为它创造了支配你生活的规范。宏观系统就是我们游泳池中的水,他称之为剧本。我们按照剧本生活,甚至不去考虑它们,甚至可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,即使我们受制于它们。
本质上,有一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剧本,会使生活变得更简单,并成为默认的生活方式。在一种依赖剧本来获得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的文化中,篡改剧本是一种背叛行为。然而,剧本本身的存在也在不断地改变着,如果我们试图在一个新的环境上恢复以前的剧本,将会有一点障碍。
创造力学者爱德华·德·博诺(Edward de Bono)称其为“自我最大化系统”(Self-Maximizing System),就好比一条河流。河流是由水根据重力定律找到最低点而形成的。当水沿着之前的水形成的路径继续流淌时,路径实际上是弯曲的,并继续冲刷河道,这就成为了未来所有水都会流淌的方式,因为这是通往地球上最低的地方的最快方式。
当剧本运行时,所有这些都没问题。当剧本不能工作,或者不断发展的剧本继续产生新问题时,自我最大化的系统只会进一步强化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。
只有意识到定义和决定我们存在并提供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的剧本、宏观系统和自我最大化系统,我们才能想象出新的剧本。
改变可能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,即使是我们假设的,默认的剧本。但当谈到改变,我们必须看到,改变剧本是我们天生的不情愿和对未知的恐惧的对抗,甚至我们的大脑都怀疑。
这是我们拒绝改变的第一个原因。这不是一种道德批判,这是人类存在的一种自然属性,经过数千年的历程,已经在我们的意识中形成了。
我们抗拒改变,因为它是不确定的、有压力的,而且违背我们的本性。
我们抵制改变,因为它破坏了我们的剧本。
原因2 :改变就是损失
当剧本不起作用时怎么办?当一个人目前的生活状态明显是破坏性的该怎么办?如果我们想要可预测性和稳定性,我们不是更倾向于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改变吗?为什么我们在不健康或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仍然抗拒改变?
在我二年级的时候,我搬了新家。新家就在城市的另一边,但我经历了一件我在那个年龄无以言表的事情。整整一天,一拖车又一拖车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。大家不断地收拾东西,搬运,卸货,直到黄昏,房子终于空了。我和母亲留下来收拾最后的东西,房子彻底打扫干净后,我们走出去,最后一次锁上门,然后开始向我们的车走去。
车道紧挨着房子,从马路一直延伸到我们家后面的车库。当我走到房子的前面,看到夏天明亮的紫色天空时,我真想停下来。母亲继续往前走。她回过头来,不知我身在何处。这时,她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了,不知为什么,我哭了起来。
为什么一个二年级的孩子会在大马路上哭?
这里有一些需要考虑的事情:当一个新物种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生存时会发生什么。在一定的时间内,生物圈包含特定的生物和植物,它们在特定的地方形成共同的特征。食物链、共生关系和生命周期决定了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。当你插入一个入侵物种,当一个陌生的生物从外部迁移进来时,它不仅仅是把自己添加到现有的生态系统中,新物种改变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。
对于我们人类来说,同质状态是理想的。我们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和一致性,这使我们的生活领域更容易驾驭。然而,正如寻求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的剧本的规范和模式一样,我们对这种同质的追求创造了新的现实。但它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个新的动态,它完全改变了我们生态系统的组成。这样的循环仍在继续。
当你养成了一个新习惯、学习了新信息、搬到一个新社区、生了一个孩子或换了一个新领导,它们会导致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,就像一个新物种进入一个生态系统。
新事物不是简单的添加。
那么,这意味着旧的东西现在已经消失了。
任何变化都会改变世界,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。即使是好的改变也是一种损失。因此,对旧事物的熟悉,可能会阻止我们以我们认为积极的方式改变。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拥有的。失去它就像下地狱一样可怕。
甚至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,我就知道有些事情结束了。我从骨子里都能感觉到。我知道这种改变,即使搬到新家好处多多,那也是一种损失。
这常常使我们无法改变,因为我们渴望它过去的样子。改变就像一个新物种入侵了我们的生态系统,重新配置我们已知的世界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熟悉的事物是容易而为人所知的。我们不想让它被破坏,我们也不想失去它。
所以,我们抵制改变。
我们拒绝改变,因为改变会带来损失。
原因3:改变是缓慢的
想象一下建造一座哥特式大教堂,我们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。那些古老的大教堂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,那些开始修建这个项目的人,那些在地面上铺设第一块石头的人,知道他们无法活着看到教堂的完工。
建造一座大教堂将是一个漫长、艰巨而复杂的过程。
建造一座大教堂,就其发展而言,有点像改变。
我们想要一个新的愿景。当我们看到一间凌乱的房间时,会很想把它收拾干净。然而,一旦我们真的插手开始干了之后,任务就变得异常艰巨。打扫房间需要一点一点地进行,房间越乱,过程就越复杂。你不能一次处理所有的混乱。你也不能一次改变所有。
因为改变是困难的,而且发生得很慢。
你想改变世界?你想改变自己的生活?你想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?这都不会一下子发生,因为改变是一个过程。它不太像一场魔术表演,而更像是几个世纪以来海浪不断冲刷出的悬崖。改变你的生活和就好比大峡谷的侵蚀过程一样漫长。
这就是变化。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缓慢的、折磨人的、毫无浪漫色彩的过程。
看到最终目标很容易。做出一个单一的决定,并拥有凝视可能性的意志力是很容易的。然而,真正做出改变是很难的。当我们真正穿过时间的艰辛走向目的地时,我们发现,穿越变化的大地呼唤着我们回头。因此,我们的反应往往是留在烂摊子里,而不是去清理它。
我们抵制改变,因为不改变会更容易。
我们拒绝改变,因为改变是困难的,而且缓慢得令人害怕。
改变是无限可能的。
你想被治愈吗?你想做出改变吗?要知道你正面临着巨大的阻力:一个困难、不舒服、缓慢的过程,加上我们对熟悉事物的倾向,以及我们对失去的恐惧,会形成一种抗拒的混合物,这单靠意志力是无法克服的。
我们宁愿留住一颗种子,也不愿把它埋在不确定之中。我们宁愿紧紧抓住脚下的土地,也不愿冒险进入未知的领域。
就像一艘困在引力轨道上的飞船,我们抗拒变化。
但要打破轨道,首先要知道是什么把我们困在这里。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内在的障碍,就可以让自己更好地踏上旅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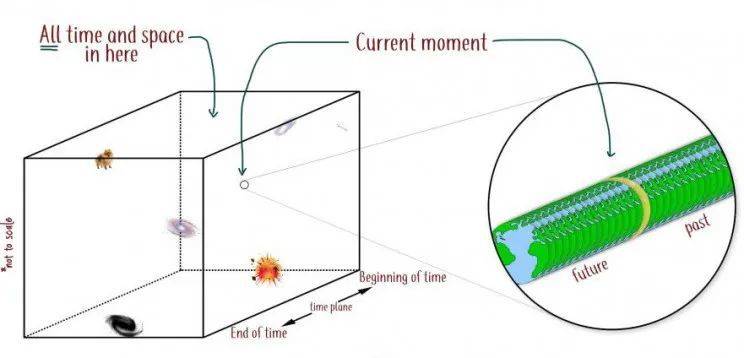




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